作者:石安浅
“上帝不响,像一切全由我定……”
《繁花》原著35万字,“不响”两字就出现了1300多次。
王家卫说:“不响”不代表沉默,它是一种留白。凡事我不想讲的、不能讲的、讲了为难自己、为难别人的——不响!”
“我只讲我能讲的,我想讲的,我讲的好的。”
在万里之外的雪国芬兰,也有这样一个“不响”的导演——阿基·考里斯马基。

(阿基·考里斯马基:为了成为名导你知道我献祭了什么吗?)
他在国内的名声可能“不响”,但在国外可是如雷贯耳。
《枯叶》
Kuolleet lehdet

他的新作《枯叶》位列《时代》杂志2023年十佳影片榜首,法国《电影手册》也将其评为年度十佳之一,考里斯马基更是凭借它夺得了当年的戛纳评审团大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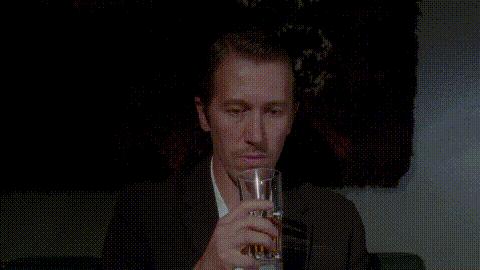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在赫尔辛基的一间酒吧里,善良的女工安莎与酒鬼霍塔里相遇了。灯火阑珊下,二人对上了眼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两个孤独的人似乎终于可以抱团取暖了。但命运对二人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。
先是霍塔里弄丢了安莎的电话号码,二人失去了彼此下落,“不响”;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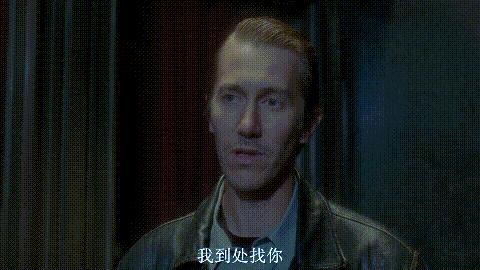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好不容易重逢后,安莎又发现了霍塔里有酗酒的恶习,二人不欢而散,“不响”;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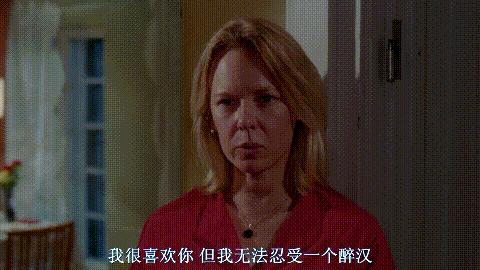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霍塔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戒酒,安莎也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结果赶路时被电车撞倒,生命垂危,依旧是“不响”。
很多不熟悉考里斯马基风格的观众初看本片时一脸懵逼。“评分凭什么这么高?”“这故事也太俗了吧!”“就这也能拿戛纳?”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这其实很正常,考里斯马基和王家卫一样,有着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。他们是纯粹的作者导演,也是迷影向导演。比起包容性和接受度更强的商业制作,他们作品的观影门槛要更高一点。爱他们的人爱的要死,不感冒的人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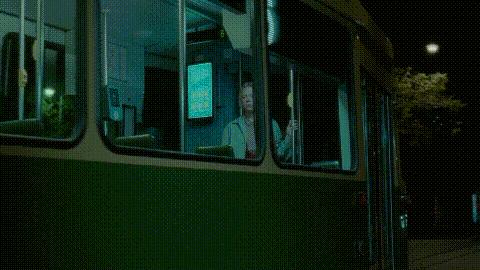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受到布列松极简主义以及北欧电影传统的影响,考里斯马基的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极简美学色彩,同时又不落俗套,独树一帜。
与王家卫酷爱的十里洋场,灯红酒绿不同,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一直在描绘繁华都市背后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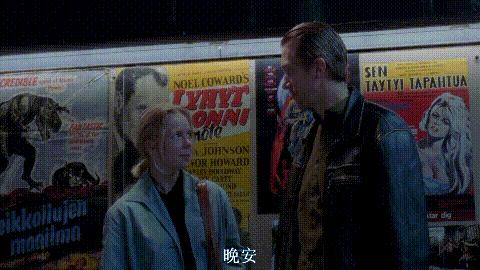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冷峻的色调与打光,木讷、迟钝、内敛的人物表演,稀疏的台词,就像芬兰的寒冬一样,给人一种压抑致郁的冷感,但影片的主题始终是对温暖与阳光的追寻。
一个人如果一直待在春暖花开的环境里,根本不会在意阳光的珍贵。只有时时刻刻暴露在冷风中的人,才会珍惜那片刻的温存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片中安莎因为将快过期的面包送给了流浪汉而被辞退。转到酒吧工作后,老板又因涉du被逮捕。不仅爱情“不响”,生活也“不响”,受挫感就像树上积累的枯叶一样,剪不断,理还乱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许多观众没搞懂片中为什么经常传出俄乌战争进展的广播声?有什么特殊意味吗?小派认为可能那是导演刻意营造的一种平静与动乱的反差感吧。就像很多人说的,“宁为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”,可在和平环境下让你做“太平犬”,那种煎熬感和麻木感其实并不比当“乱世人”轻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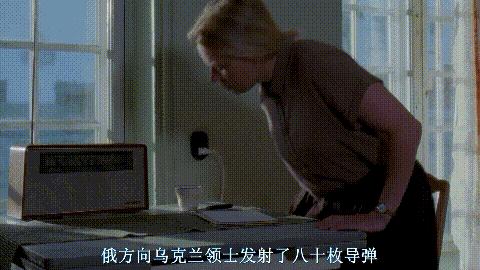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安莎和霍塔里便身处于“太平犬”的困境里。
物质匮乏,精神贫瘠,生活中没有惊喜和欢愉,只有数不尽的寂寥与惆怅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本片第57分钟,安莎救下了一只小狗。也是从那时起,电影里那种难熬的孤独感开始悄悄褪去,霍塔里终于愿意为安莎戒掉酗酒的毛病,安莎的脸上也开始出现微微的笑容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小狗是考里斯马基电影里必不可少的意象,它代表着希望。每当有小狗出现时,就代表电影人物命运的转机的带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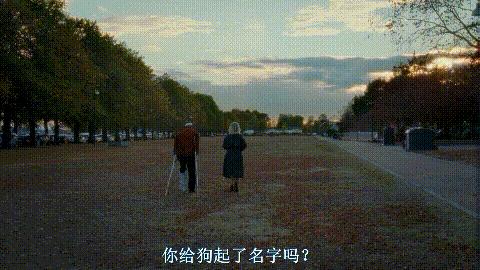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结尾,霍塔里终于苏醒。安莎接他出院,两个人牵着狗走在阳光下,阳光刺破了冷峻,枯叶落尽,一切终于开始向“响”的方向好转。
初看本片时,可能会因影片过于沉闷而放弃。耐下心来,放空自己,结尾致郁会变治愈,“不响”也会变成“响”。

(电影《枯叶》截影)
最后再讲一个小tip。和很多作者导演一样,考里斯马基也是一个偏执狂。他有条不成文的规矩,拍电影时长绝不会超过80分钟。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“这个时长是我所能忍受烟瘾的极限”。
图片源于网络








